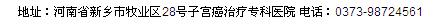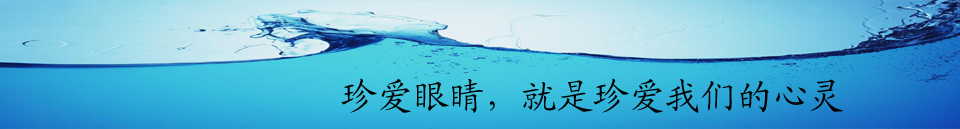
一个轻度斜视者的记忆吴向东
点击一起加入“万字阅读挑战计划”!
一个轻度斜视者的记忆
作者
吴向东
摄影
吴向东
选自《花城》年2期
我出生的年代刚好赶上了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而且正遇到武汉罕见的严冬。虽说武汉是火炉,可它的冬天却冷得一点也不含糊。也许我命中就是要和“饿”字结缘。据母亲说,我出生后她一点奶水都没有。父亲咬了咬牙,跑了十里路去了附近郊区的农村,用半个月的工资,好说歹说,在一个农村老婆婆手里买了一只,看上去似乎还算肥硕的老母鸡,准备给母亲发奶。
父亲知道在那个年代一只这样的母鸡可救活一家人的命。所以回来的路上,他用蓝色的工装大棉袄把母鸡紧紧搂在怀里。我长大后,父亲曾笑呵呵地对我说,就是搂我母亲也从没这样深情过。
母亲说,从父亲离开家,踏上买鸡的征程后,她的口腔就一直饱含着口水,翘盼着父亲的归来。母亲当时清楚地记得,父亲卷着一阵寒风和雪花跌入家门,然后就趴在床上不停抽动着双肩,用拳头击打着床沿。母亲吓得口水全无,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的脆弱。她印象中的父亲是那个在大学毕业典礼上慷慨激昂地迎接祖国召唤的学生会主席。
父亲哽咽得像个孩子似的向母亲哭诉着,那只老母鸡怎样被他的大棉袄捂得拉了一泡热屎,他本能地松了手。老母鸡欢快得意地挣脱了父亲,跳到雪地上飞奔了起来。父亲被这突然的热屎搞得呆若木鸡,许久才回过神。当他在雪地上歇斯底里地狂追的时候,那老母鸡早已不见踪影。
母亲说,她至今都记得当时那只闻鸡屎味不见鸡肉香的悲凉。直呼“向东太可怜,向东太可怜”。
我的名字叫吴向东。这是父母亲在新婚之夜行动前就早已想好的名字。母亲说我可怜还有更多的理由。因为他们当时都认为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马上要降临了,他们要加紧为共产主义生育接班人。可是从我在母亲体内扎根后,灾害就降临在我们可爱的祖国。我们的牛肉、土豆都送给了“苏修帝国主义”,据后来小学老师说,送给“苏修”的苹果还要用尺量,太大太小都不行。真是气死我了。好在母亲说她怀我时萝卜吃得特别多。因为当时苏联专家都撤了,父母亲所在的军工厂基本停建。父亲就发挥了农民儿子的长处,偷偷在附近的空地里种起了萝卜。用现在的说法萝卜可是土人参,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是吃多了那产生的气体也够受。母亲常抱怨说,就是那尴尬的气体使她一个出生在江南水乡的娇女人在父亲面前失去了神秘。长大后的我也觉得是那萝卜害得我成了罗圈腿,直到后来看到年迈的父亲迈着“O字形”的腿摇摇晃晃的,我才知道那的确不是萝卜惹的祸。
……
自然灾害很快过去,祖国又开始显现出生机。可是父母工作越来越忙了,为了搞好革命工作,他们已经无力照料我了。军工厂本身就在武汉市郊,条件很差,根本就不像现在还有什么幼儿园一说。因此父母亲上班后就只能把我放在摇窝中(武汉话,其实就是摇篮)。父亲担心我一人在家会害怕,每次出门时都把灯打开,好像这样能给我一点光明,使他的内心会好受一些。
可是时间一久,母亲首先发现问题。因为她发现我平时很喜欢斜眼看人,有时斜得眼珠都回不来了,甚至有时是一眼正,一眼斜,不知道在看谁。一句话,我就是成了武汉人所说的“瞟眼”。
母亲认定这是由于我躺在摇窝中长期斜眼看灯造成的,为此她和父亲大吵起来,骂父亲无知。当时父亲也没敢还嘴,他觉得这可能是他的错。父亲是学热处理专业的,他深谙金属也是有弯曲记忆的。
可以说这个“瞟眼”对我一生影响极大,特别是在追女孩子后,它使我有了很大的自卑感。比如,我在和女孩子说话时会时常不断在内心问自己眼睛瞟了没有?聊天时我盯女孩子的时间绝对不能太久,要时常有意识转睛看看其他的目标,否则,我的眼珠会不由自主地在眼眶里缓缓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随之停留在眼眶的角落。
上大学时,我曾试探我的女朋友说,你知道为什么有人说我高傲,说我和人谈话心不在焉吗?
女友很爽快地回答说:“你是个‘瞟眼’呗。”
听她这一说我吓得够呛,忙问:“你看到我瞟了?”
“看到了,有时还瞟得很厉害呢,你那些努力都是徒劳!”
当时我真是又悲哀又对她感激流涕。
大学毕业我们分手时她曾悄悄告诉我,其实她的眼也有点瞟,只不过她有绝招,那就是一旦感觉自己眼神开始不对时,要猛地一甩头,就可把眼珠甩回来。她说完后我才如梦方醒。难怪她平常老甩头,特别是在公众场合演讲的时候才甩得厉害呢。
二
我的外孙是个斜眼?
远在北京的我外婆听到这一消息立刻从北京赶到了武汉。她很难相信她的女儿和她的外孙是住在这样一间低矮破陋的平房里。那晚,外婆和母亲进行了彻夜的长谈。其实外婆一开始就反对母亲和父亲的结合。这不光因为父亲是来自农民家庭,更因为她发现父亲是一个对政治有着极高热情和抱负的人。外婆的半生经历让她对凡是牵涉到政治的东西都感到恐慌。当然最主要的是她认为,是父亲把她女儿拐到了这偏僻荒凉的地方。
本来在外婆印象中,武汉也是一个和上海差不多的城市,甚至在民国时还一度成为“国都”,再加上父亲当时吹嘘说是去武汉的国防工办报到,这使外婆产生了一点小小的遐想。在外婆印象中,国防工办那起码也是应该带有点欧式建筑风格的地方。她记得北伐时那些和国防有联系的国民党各部都是在租界的洋楼办公的。
外婆对和上海相似的城市都有好感。她不喜欢北京,不喜欢那不是朱红就是暗灰色的城墙,不喜欢那油油的自以为是的京腔。要不是文化部点名叫外公去北京,她是肯定不会从上海去北京的。当然她不可能想到共产党的国防单位是真正的国防,都往山沟里钻,这可能和共产党起家时养成的习惯有关。当父亲嘟囔着说他已经够幸运了,最起码和家人可以联系,不像有的同学分到核工业部,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外婆听后便生气地说,你们把我外孙都搞成了斜眼,还有理了?外婆说完这话,躺在摇窝中的我突然哭了,不是哇哇大哭的那种,而是属于抽泣类。三个大人都诧异地看着我……
外婆没多停留,第二天就带着我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很多年后,也就是“文革”期间外婆艰难得没米下锅时,我才从外婆对往日幸福生活的追忆中得知,外婆对斜眼特别忌讳。当年她在著名私立学校大夏大学(今华东师大前身)读书时,爱慕上一个很有才华的《申报》记者,她是从报纸上那美妙的文章中认识他的。后来他们约好了在上海外滩见面,这情景有点像现在的网友们见面。
外婆本来就是大夏大学的美女,再加上第一次和男人约会的羞涩,使伫立在落日映照下黄浦江畔的她,显得格外动人。反正据外婆说当时那小子是看傻了,一个你好的“你”字断断续续说了有半分钟。起先外婆还很有点得意,认为连《申报》的大记者都被她“魅”成了口吃。可是当他们在锦江大饭店的西餐厅坐定后,外婆极其失望地发现,这小子的口吃虽然不像初见面时那么严重,可他的确是个磕巴。按外婆当时的说法,就算他是磕巴,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再说,磕巴有时也显得挺憨厚可爱。
的确,这位记者的文章很吸引外婆,他的那些小资情调的散文常惹得外婆泪水涟涟。可是,外婆不久又不幸地发现这位仁兄不仅口吃还斜眼,而当时他斜的方向又正好也坐着一位美女。外婆知道他并不是真心想看那美女,因为那只代表心灵的眼睛是始终在外婆这一边的。尽管那只偏离正常位置的眼睛其实什么也看不到,外婆还是礼貌地稍坐了会,便起身和那位仁兄握手告别了。
我终于随外婆来到了我们可爱的首都北京。家中的大姨、小姨还有一个据说是远房表舅都对我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只有外公对我的到来好像不太欢迎。特别是在他听说我的名字叫吴向东后,狠狠皱了皱眉头,说,这是口号还是人名?肯定是那农民儿子起的。外公老是称我父亲是农民的儿子,就是在我懂事后也未改变这样的称呼。
外婆很快带着我奔波医院,力图能够挽回她认为是父亲带给我的恶果。在医院采取矫正的同时,胡同有个前清遗留下的太监悄悄告诉外婆,说过去宫内有个阿哥也是眼睛有这个毛病,结果太医告诉皇后,每当阿哥眼睛走神时,要对阿哥大吼一声,那阿哥的眼珠后来果然归位。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北京东四胡同那个本是很幽静的四合院内,怒吼“向东”名字的声音不绝于耳。顷刻“向东”在那条胡同成了一个名人。
有时怒吼“向东”的声音并没有阻止我眼球运动的坚定步伐,反而把作画中的外公吓了一大跳。他再也忍受不了了,嚷着要改我的名。当然大名是亲生父母来定的,是要在公安局登记的,这个外公不是不知道。所以他只能在小名上做文章。全家为此还召开了一个关于向东小名的讨论会。外公好像对此很有兴致,专门在四合院内的一棵老槐树下悬挂起一块小黑板。外公站在黑板前,好像又找回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流落到西南教书时的感觉,很是心潮澎湃。可是会议刚开始就结束了。因为大姨首先提出了一个大家一致感到欢欣鼓舞的名字:宝宝!
外公有点失落,他觉得这个名字本应该出自他口才对。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自从我叫“宝宝”后,我的眼珠特别听外婆的使唤,可能是这个名字很有爱意吧。总之,东四胡同那个四合院从此平静了许多,偶尔响起一两声呼唤,大家还觉得院内倒有点人气。
可是细心的外婆发现,虽然外孙斜眼的频率少了许多,但要断根就显得很困难。在医院的医生也感无能为力时,医生突然问了外婆一句:你们家族有过斜眼吗?这一问,吓了外婆一跳。她忽然想起她那富甲江南的爷爷也是个斜眼。她开始醒悟到女婿后天造成的错误可以更改,可遗传的基因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她不由得对女婿产生了歉意。
据外婆后来回忆说,那些日子她常想起她的爷爷和那斜眼加口吃的《申报》记者,据说这位记者后来做了蒋纬国的高参去了台湾。外婆明白了,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学识。
从那以后,我的日子变得快乐了起来。长到三岁后,就再没有了“怒吼”声,替之的是外婆每天晚上睡觉给我讲《安徒生的童话》《伊索寓言》和唱《茉莉花》。我还有了很多玩具和彩色画报,这是那个年代的很多孩子不敢想的事,就是我妹妹年出生后,她玩的玩具也还是我那时留下的。
外公替我改名时用过的小黑板也派上了大用场。每天太阳刚刚升起时,外婆就把那块小黑板挂在那个老槐树下,教我和我那个表舅学英语。外婆的中学是在上海的一个教会学校,她那磁性纯正的伦敦发音惹得同院的一个外文出版社的编辑都自叹不如。
可是外婆这样一个知识女性却没有工作,为此外婆一生都嫉恨外公。照说像外公这样一个还算得上是江南才子的人应该没有什么大男子主义的。可是他却偏偏极力反对外婆出去工作。当外文出版社的领导来请外婆工作时,外公就会恼怒地说,你以为我连老婆都养不起吗?搞得来人一脸灰溜溜。我懂事后外婆告诉我,其实外公是对外婆这样美貌的女人出去工作不放心。
在北京的几年生活基本上都是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受外婆的影响,养成了喜欢吃奶油、冰淇淋、肉松的奢侈习惯,这使得我后来回武汉后痛苦了许久。当然也有些不愉快的经历,那就是和我那个不知是近房还是远房的表舅的关系。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我的表舅。可能是因为他只比我大十岁,也可能是我们的血缘关系较远。反正在我懂事后的记忆中他老是欺负我。最可气的是每次大姨帮我洗澡,他会趁大姨起身去拿什么肥皂毛巾等物的时候,在旁边拉我的小鸡鸡,拉得老长老长,然后再突然松手,像是玩橡皮筋。当我哇哇大哭时,他却在一旁得意地嘿嘿直笑。这个恶作剧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非常不情愿地做了包皮过长的环切割手术;二是我至今都有双手护着鸡鸡睡觉的难看的睡姿,为此结婚后引得妻子呵呵直笑,说好像谁稀罕你那玩意似的。
……
四
武汉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城市,也是一座外观美丽有着厚重历史沉淀的城市。当火车轰隆隆从武汉长江大桥上驶过时,你便会看到那龟蛇锁大江的气势以及在宽阔湍急的江面上航行的轮船所飘出的带有沧桑感的浓烟。特别是在深夜,居住在武汉许多地方的居民,都可听到那从江面隐约传来的江轮的汽笛声和江汉关钟楼的大钟准时发出的沉重而洪亮的钟声。
当那厚重金属碰撞所产生的深沉洪亮的声音飘荡在夜深的城市上空时,市民们对这个城市便会产生一种温馨的,一种内心有依托的情感。江汉关的钟声经常让我思念住在江北岸汉口武胜路卫东巷的外婆。
外婆来到武汉后并没有和我父母亲住多久,便带着大姨小姨和表舅在汉口武胜路卫东巷租了两间木板搭制的小阁楼住了下来。我没能和外婆住在一起,虽然我表示出了要和外婆住的强烈愿望,可是我表现得越强烈,父母亲的意志就越坚决。
我对父母是有着强烈的陌生感的,这种陌生感一直伴随至今。我很少会像我后来的妹妹那样主动蜷曲在父母的环抱享受父母的温情。这种蜷曲温情需求我一直留给了我在卫东巷的外婆。这不知道是那为革命一直激情四射的父母的损失还是我终身的遗憾。90年代,当我怀揣挣大钱的梦想踏上南粤大地时,我的女儿遭遇了我幼时同样的命运。此时我才能体味些生活其中的酸辣和对命运沧桑的无奈。
外婆是见过世面的女人。她一眼看出卫东巷这一片木制楼阁群就是30年代的产物,虽然破旧却也很有格调。特别是她租的二楼的两间房还有一个突出的临街小洋台,站在洋台上你时常可以感到浓厚的市井气息。当然这里的夜间也可以听到江汉关的钟声,这叫外婆想起了上海黄浦江畔的一些弄堂。为此我父母亲也付出了相当的租金。我外公那时已经停发了工资,全家人就靠我父母亲加起来不到百元的工资生活。
外婆租的房子是木板搭制的,所以屋内贴满了各色报纸,这是那个年代流行的装饰。它既可以挡风寒也有些许美观的韵味。那满屋黄黄的报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脑子里不断萦绕的画面。我很思念我的外婆,我很怀念蜷曲在外婆的怀中听她唱那首《茉莉花》。外婆的身上至今都能散发出一种奶油的香味,那香味让你即使身处在这木板的阁楼里,也能体味出一种独特的滋味。
本来外婆和表舅、大姨和小姨各住在一间房。可是很快大姨小姨嚷着要搬到学校去住,因为在她们房间隔壁住的是一对新婚夫妇。男的是王家巷的码头工人,女的是国棉四厂的女工。那薄薄的木板墙怎能阻挡住隔壁人家夜间叮叮当当的屙尿声和嘭嘭的屁声,以及……呢?她们都是高中生了,反证法早已学会。所以她们不但每次解决得非常不痛快,还经常是两人羞得满面通红,都不敢看对方。好在不久她们都随着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分别去了咸宁和洪湖农村。
表舅很快就占领了大姨小姨的房间,而且他对各种声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最后都能分辨出这各类声响来之于谁。不过他本已出现好转的尿床现象又开始严重了。后来我发现他的床单上经常出现小地图般的污迹,我可以肯定那绝不是尿迹,因为对他的尿地图我老早就耳熟能详了。
其实男孩子对下三路的东西天生是很好奇的。有一次星期天外婆接我去卫东巷吃饭。晚上我便又和表舅同居一室。深夜,隔壁在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后,出现了剧烈的震动,随之而来的还有男人女人痛苦的叫声。
我问表舅隔壁人在干什么?
表舅说他们在打架。
说着表舅掀开贴在墙上的报纸,命令我用那只比较端正的眼睛贴着被他明显弄宽了的木板缝往隔壁看:好家伙,那男人果然在欺负女人。奇怪的是被欺负的女人哭喊可以理解,而欺负人的男人也居然是一脸痛苦模样。我不懂。
表舅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快到下面找房东老婆婆劝架去,要不会出人命的。
我飞奔下楼。
隔壁的“打架声”在房东老婆婆急促的敲门声中,戛然而止。随后便听到那隔壁男人的叫骂声:你这个死婆婆是不是有点呸啊(武汉话缺德的意思)。
从此,那房东婆婆总说我这个“瞟眼”伢子是人小鬼大。每当这时表舅就会在一边偷笑,那年他已十四岁。说实话,我总对我这个表舅有些好奇,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表”字来源于何方。依据我后来对外公的性格的判断,他怎会收养一个其他亲戚的孩子?我曾问过我的母亲此事,可母亲对此也是闪烁其词,她只是淡淡地告诉我,表舅是外婆弟弟的孩子,舅妈生她后不久就因大出血死掉了。
房东太太不久真的死了。那是因为几天后武汉下了一场特大暴雨,整个卫东巷都被浸没在齐腰的雨水中。房东老婆婆住在一楼,那些天她整日在水中走来走去。有一次她走着,走着,她突然撇开腿停立水中一动不动。
我问婆婆,你在干什么啊?
她说:“没什么,屙尿,屙尿。呵呵……”随后一阵寒噤又做她的事去了。
可能就是这泡尿,不知使水中的什么病毒钻入了她的体内。当晚她就发高烧,第二天就去世了。我们都很悲哀,特别是前几天还骂过死婆婆的那个码头工人。
五
房东老太太去世后,她的儿子继承了房产。这小子是个长期混迹于武汉民众乐园的地痞,他看出外婆身上有点油水,便嚷着要提高外婆的房租。
外婆很喜欢这套木阁楼,但又不想再给我父母亲添麻烦。外婆本想当掉外公收藏的一些明清时期的字画,可是犹豫再三,最终选择了在别人都该退休的年龄,第一次参加了革命工作。
外婆是在汉口满春里一个街道玻璃器皿厂找到了一份打磨玻璃的工作的。尽管上班的第一天外婆换上了从母亲那里要来的最旧的工作服,可是当外婆走进那飞扬着玻璃粉尘的车间时,仍然引起了车间内那些爹爹婆婆们的一阵不小的轰动。据后来的那些爹爹婆婆开玩笑说,那个晚上好几个鳏居的爹爹们都在那里压床板没睡好觉。
从那天起,外婆每天戴着一个大口罩在车间里打磨玻璃,车间内刺耳的玻璃摩擦声,整个满春里都听得到,可是外婆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依然神情非常专注地干着手中的活。我至今都记得外婆那优美的静静的身影在悬浮的玻璃粉尘的车间里艰难晃动的情景。
我很难想象受过教会学校教育,上过大学的外婆能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求生存,此时她的内心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力量。可是外婆坚持了下来,而且还赢得了那些爹爹婆婆们的尊重,他们亲热地称她为:蒋婆婆。
我的外婆叫蒋丽容。一个下江人,又姓蒋,这让那个时代的人会产生很多联想。据外婆说,刚进街道工厂时,的确有几个爹爹婆婆开她的玩笑,说她可能是蒋该死家的人。每当这时,外婆只是一笑而之。外婆的言语很少,她只是认真做好别人分配给她的工作。玻璃厂的厂长很快发现,外婆会算账,她还能读懂吹出的玻璃器皿上刻有的英文商标。不久外婆就脱离了现场的劳作,做起了会计。外婆做了会计后,厂长又发现外婆居然极其善于和协作单位打交道,后来他干脆让外婆做了副厂长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我记得外婆当会计的那天心情非常好,她喜滋滋对我说:“宝宝,知识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用的东西。”
月底发工资是外婆最高兴的日子,那天外婆会早早通知我在卫东巷等候。下班后,外婆便会手脚利索地,换上她早上出门时就准备好了的,平时最喜欢的衣服,拉着我就去江汉路的四季美汤包馆。那时表舅已经被外婆“遣送”去住校了,因为外婆最终了解到表舅在那次“劝架”中所扮演的角色。
外婆带我上了四季美的二楼,选一个靠近临街窗口的位坐下,在点上二两一笼汤包后,外婆便会饶有兴致地欣赏着窗外川流不息的人群和马路对面亨达利表行精美的哥特式建筑。武汉的江汉路是最有殖民色彩的一条街,它和上海的街道有许多形似之处,这也许就是外婆很喜欢坐在这里的原因。我不知道此时的外婆是否在想那远在戈壁滩的外公,关于他们之间的情感我始终很难弄懂。他们那张拍摄于30年代的婚纱照如今已深深刻在了他们的墓碑上,每一个经过那里的人都会驻足侧目;每一个人都会在猜测这才子佳人照片背后的爱情故事。可是我却感到他们之间并非彼此相爱。他们不仅彼此淡漠,甚至连他们在故乡的亲人都未曾联系过。
改革开放后不久,外婆很新潮地要求家人把她送去养老院。养老院是在武汉非常偏僻而幽静的一个地方。可是外婆这么精明的人晚年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我未离开武汉时,每个月都会从养老院把外婆接到四季美。还是坐在那个我们过去常坐过的临街的窗口旁,还是二两一笼的汤包。虽然此时外婆已经感受不到如今的江汉路的繁华,也听不到江汉关的钟声了,可是当热腾腾的汤包一端上来,外婆便会显得话特别多,可惜很多我都听不懂。因为外婆已经把她二十岁以后的生活几乎全忘掉了。她现在只会说老家周庄话和已含糊不清的伦敦英语了,有次居然还喊我“阿郑”。
母亲常说外婆有一个极其幸运的晚年!
六
外公去了新疆后,几乎和家里断绝了联系。偶尔来一封信,也是向母亲要钱。我的外婆在我们面前也几乎不提起外公,仿佛在她的世界里根本没有这个人。
我的父亲非常不满意外婆这一点。也许他从男人的角度出发,觉得此时的外公更需要外婆的关照。父亲甚至还觉得我母亲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不正常。他说这一家兄弟姐妹之间客客气气的简直像个外人。父亲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因为我父亲一直对我外公外婆这么多年不回家乡探望,甚至不和家乡的亲人联系感到不解,由此他还得出了江浙人皆薄情寡义的结论。他甚至可能对我的母亲也产生了类似的联想。
我曾给我外公写过一封信,因为那时我正在学素描,我把我画的画寄给外公,希望他能提提意见。外公很快回复了我。外公信中的笔迹透露出一种龙飞凤舞的轻盈,他喋喋不休地同我讲述了一大通,让我似懂非懂的关于艺术鉴赏的道理。可是在信结束时,外公没有忘记叮嘱我说,以后在信封上写郑克基收就行,不要加“同志”二字,这对你将来不好。母亲看到这封信时,不由得眼圈潮红了起来。
父亲曾多次提出要去石河子看外公,因为父亲每年都有去乌鲁木齐出差的机会。可母亲是极力反对父亲去石河子看外公的。事实上不仅母亲反对,就连外婆知道此事后也反对,这叫父亲当时哭笑不得。父亲的举动在当时的境况下算是一个相当仗义的行为。也许是外公一直瞧不起父亲,所以父亲更想表现出男人仗义的气概。我至今也不知道外婆为何反对父亲去探望外公。也许外婆能够想象得出外公在戈壁荒漠的落魄,而她又不想让女婿看到她丈夫狼狈的模样?也许外婆知道我父母此时已经手头拮据,而不想让我父母再破费?但是外公的这封信,最起码改变了母亲的主意。
这是一个关系到外公命运的改变。因为父亲遇到外公时,外公已经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父亲的到来使病危中的外公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外公直呼苍天有眼,使他在临终之际身边有一个亲人,不会变成孤魂野鬼,被人抛尸荒郊野岭。
外公总算是在有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下去世的。可父亲当时也只能趁云低夜寒之时,和几个一起劳改的北京人把外公偷偷抬到戈壁的盐碱地里草草掩埋了。
墓地是设在一个面向东南方向的一个小山丘上,这是按照外公生前的意思办的。因为东南方有外公的老家,江苏的一个小镇:周庄。
……
我们这一群人都是第一次回老家。过去我曾经常缠着外公外婆带我回他们常挂在嘴边的江南水乡去看看,可是他们都摇头拒绝。我当时并不认同我父亲说的二老薄情寡义的观点,以为那多半是受经济所累。而现在我终于渐渐理解了,他们为何会对如此婀娜的家乡时时溢露出来的那种淡漠。
在回程的路上,我们全都望着江南那阴阴的细雨沉默着。外婆弟弟被镇压一事,我们都是第一次听说,我们似乎感到那蒙在外公外婆身上的历史帷幕才刚拉开。一路上,我一直在观察表舅。我发现表舅正用一种艺术家的哀怨还有些许贪婪的眼神注视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田野。在表舅痛彻心扉,捶胸跌足之后,他央求老人帮他寻找他父母的遗骨。可是老人告诉他:他母亲的墓地处如今已经建成了商业旅游一条街,至于他父亲的遗骨政府当时就另作处理肯定找不到了。
车在江南乡间湿滑的公路上行驶了很久后,我忽然看到车窗外不远处有一个大大的牌楼,牌楼的顶端除了刻有龙凤呈祥的图案外,还写着两个鎏金大字:周庄。我竭力甩了下脑袋想把眼球调正,我本以为是我那斜眼产生了错觉,可我最终还是肯定那的确是“周庄”二字。
此时,我才忽然明白,那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江南水乡其实离周庄还很远。
吴向东《失重的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