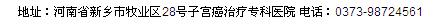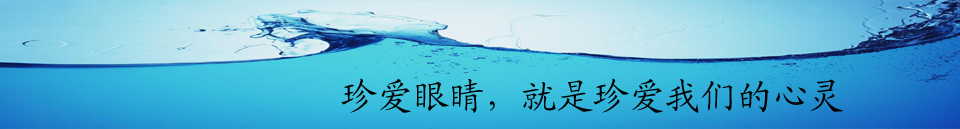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那时花开
又要跟最不喜欢却又离不了的地方——医院打交道了。
一年复查的时间到了。
疫情一度成为了一个拖延的借口。拖来拖去,眼看防疫在往常态化发展,再拖延没有意义,对自己和家人也不负责任。
鼓足勇气预约了门诊,准备住院做脑血管造影复查。
由于防疫的需要,住院前需要做核酸检测,拿到阴性的检测结果才能办理住院手续。
疫情并没有走远,像一个幽灵。
陪护
由于疫情,医院住院部封闭管理谢绝探视,每个需要陪护的病人只能有一个陪护人员,也需要先做核酸检测。
这跟原先那种基本随时可以探视的“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大不相同。
挺好的,清净。
病人由家属陪护大概算中国特色吧。可是,除了那些久病成医、“自学成才”的病人家属,一般家属有啥护理经验呢?
虽然家属的陪伴能够一定程度上抚慰病人的心情,但是病人的第一需求是被治愈。专业的医护人员才是病人最信赖的。
护理人员不够,为什么不能适当增加编制呢?反正住一次院,对很多手术来讲,最大的费用是材料费,什么膝关节置换,什么心脏搭支架,凡是需要往身体里放“东西”的,都是价格不菲的,而且自费比例不低。
相比起来,手术费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即使加上专业人员的护理费,对很多病人和家属来说也是更好的选择吧。毕竟请假来陪护家属也是要承担经济损失的,还会耽误工作。
非要进天价的重症监护室,才能享受这种“待遇”吗?
幸好还有护工这个行业的存在,填补了空白。又一个中国特色。
据护工们讲,出于防疫的需要,“游兵散勇”类的护工已经大大减少,由护理公司统一医院的认可。今年由于受疫情影响,服务业普遍不景气,护工的数量比往年更多,有时会无工可上。
鉴于脑血管造影后6个小时内有切口的右腿不能移动,24小时内不可以下床,在家属陪护和护工陪护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很方便快捷,提前一小时打个电话,医院的护理公司的主管就把护工领来了,是个看上去朴实、本分的大姐,有一定的经验,知道该做什么,特别节俭,把各种生活的需求降到了最低的极限,一个馒头就着咸菜,再冲杯麦片,就是一顿晚餐。
不是所有的护工都朴实本分。
后来搬去的病房里有个男护工,看上去不到四十岁,比一般的护工要年轻,好像还有点见识的样子,该干的活倒是都干了,但话多得令人厌烦,不知道考虑病人的尊严,完全不懂分寸感为何物。
他跟上一个服务的病人和护理公司之间有什么纠纷,于是逢人便骂公司主管,一次次重复自己的故事,觉得自己很弱势很卑微,然后愤愤地说:“为什么中美不开战呢?为什么不来一场运动呢?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我非把她整死!”
我惊了。
这是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妄想“乱中取胜”的吧,也只在网络上见过此等“高手”,现实生活中尚未见到“活的”。
有时候,他会在病房里自己租来的狭小的折叠床上打坐,或一字一蹦地念经文。就这,还是一直在“修行”的结果。
从此之后,我想自己再也不会跟网络喷子们生气了,无视是最好的选择,讲不赢道理的。
医院的环境
第一个病房没有卫生间,厕所就在对面,味道有点冲。里面隔间的门锁都坏掉了,关不上。
我开玩笑地跟护士投诉:“这不是侵犯人权吗?这么久了你们不知道锁坏掉了吗?”
护士的脸有点红了,表示一直没有人投诉,因此不知情,于是赶快给总务处打了电话让人来修。
过了几天,仍然是那个状态,不知道修了又坏了,还是没有修好,或者是根本没修。
医院,流水的病人,忍吧。
我试着说服自己:你看看咱们社会主义的医疗体系在此次疫情中表现是多么的好!咱是来治病的,不是来享受的。
医院,这么说吧,N年前一个“水土不服”、坚信私立诊所一定比医院好的老外朋友去治牙髓炎,被不称职的年轻牙科医生险些要了命之后,终于有点明白了中国特色的医疗体系,也给我上了活生生的一课。
后来转到一个男女混住的病房,带了卫生间的。
虽然有帘子间隔,仍有诸多不便。病床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大概就顾不了其他了。3个病人,如果再加上3个护工,病房显得比较拥挤,完全没有舒适可言。
病人,大概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一个没有性别的“生物”。
病房走廊上的大门是安装了门禁的,要的就是疫情之下,病人和陪护进出都不自由,避免带来风险。
观察了几天,发现这个科室的管理并不严格,有的时间段有护士在门口值守,负责给进出的病人、家属和陪护开门、关门,登记进出的时间。
其他时间段就没太有人管了,只要有人按铃,哪个护士在护士站听到铃响,就会给开门,让人进来或出去,并不多问。
病人、家属或护工在走廊里溜达,不带口罩也没有人管,偶尔会有严格的护士吼上一嗓子,其他护士都不管。在各自的病房内也不要求病人带口罩。
听护工们讲,这个科的病房管理算是不严的,有的科病房管理严格,对进出也控制得很严。
可见疫情一好转,医院管理上难免松懈。
心里庆幸疫情基本算是被控制了吧,否则这种管理方式肯定是不行的,隐患不少。
有一件很大的病房,里面空荡荡的,偶尔有个病人,外面挂的牌子写着“隔离病房”,问过才知道,是用于从急诊转来的、还未来得及做核酸检测的,等收到了核酸检测结果,才会被转入病房。
病友
第二次换房,其他2个病友都是男性。
我调侃自己:跟陌生的异性“同居”,也是少见的体验了,心理上不会放松,免得一个人自怨自艾,胡思乱想。
其中一个病友从本院新楼的其他科室转来。新楼的科室(比如内分泌科、妇产科等)病房条件很好,是宽敞明亮的2人间。
看来医院的条件也是能逐步改善的。
从内分泌科转到了“鬼见愁”的神经外科,他顿时觉得从天堂坠入了地狱,一个六十多岁知天命的老同志了,秒变中二。
我不厚道地笑了。
所以人千万不能生活地太舒适了,好日子往苦日子过,太难了。
下次争气点,得病得个能住上新楼的病,也体验一下新楼的高级病房。(呸呸呸!不吉利。)
这位怕痛的病友惴惴不安地向我打听血管造影中的股动脉穿刺是不是会痛。刚刚做过一次的我表示:只会在刚开始和结束时痛上几秒,很短的,可以忍受。
他稍微松了口气。
想不到咱也是有经验的、可以给别人提供信息的病友了。
这位病友只知道术后6小时右腿不能动,竟然没有人告诉他24小时不能下床(或者他自己没听清楚)。
当他度时如年,在盘算再过多少分钟就可以到处乱窜了,我只好告诉他:“大哥,24小时内你都不能下床。”
他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我又偷偷地乐了。
额......医院为什么不能搞个书面的告知呢?万一有个什么差池,谁负责呢?
另一个病友更加特殊,是个韩国人,常年在本地工作,会讲中文。他说在发病前的十天里,工作太过玩儿命,于是导致脑出血,语气有些沉重。
一个外国人,在疫情期间突发疾病险些丧命,家人都不在身边,也是不容易的。据说他做完手术的第一天,由于疼痛,加上脾气火爆,把连接监护器的管子都给扯了,整晚不睡,搅得两边的病友和家属不得安宁。
还好没赶上。我入住时,他已经是术后好几天了,除了脑袋上贴着纱布,显得比较正常了。
韩国欧巴完全不遵医嘱,坚持除了王老吉和“无糖”可乐,其他的不喝。结果护士来测血糖,一测19点几,被护士狠狠威胁了一下,才有所收敛。
吃的饭更是红红的一层辣椒和肉,让人不能直视。
他大多数时间都盘着腿在床上低头狠刷手机,没见他闭目养神过。
总之,怎么不健康,怎么不利于病情恢复,就怎么来。见识了!
难道中国人养病跟外国人养病不同,也像中国女人要坐月子,而外国女人不用坐月子?
但是血糖指数是不会骗人的,哪有什么“无糖”饮料呢?喝白水是“祖训”,是有道理的。
当我被推出病房去做手术时,他向我做了一个好运的手势。
有点感动。
那位来自“天堂”的病友也慢慢接受了环境,会聊起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聊起此次住院主要是累的,儿子和媳妇都是呼吸科的医生,疫情发生这几个月基本顾不上家,两个孩子只好由爷爷奶奶照顾。
听到他说儿子获得了精神荣誉称号和不菲的现金奖励,心里也是替他们家高兴的,觉得完全应该得到。
这大概是病友之间的同病相怜了吧。
男病友也是有好处的,虽然倾诉欲丝毫不低于女病友,但是不会家长里短的问东问西,好奇心没有那么强。
只好如此安慰自己。
病人家属
过了2天,术后一切正常,我试着要求晚上回家休息睡觉,一早来输液,被主任一口拒绝,说:“有个病人非要回家,医院就发生了血栓......"
那好吧,道理都懂,我忍。
被转入了条件好一些的另一间病房,朝阳,敞亮,有一个女病人。
终于从男生宿舍转到“女生宿舍”了,尤其是可以摆脱那个烦人而话多的男护工,心情好了一些。
女病人跟我年龄相近,郊区的,反应不似常人,身材很健壮,白白胖胖,但行动和说话缓慢,一只眼睛也有些斜视,一看就是手术后遗症。
“女生宿舍”还是有男生,是她先生。
他问我病情,并且问动脉瘤的位置。
位置?我使劲儿想了一下,印象里好像是后交通什么的,具体不太懂,也没太留意。
顿时觉得自己是个相当不合格的病人,感受到了学渣般的惭愧。
他笑了,说:“这说明你长的位置不是要害。非要害部位的动脉瘤,即使破裂了后果也不太可怕,没破裂的话做完介入栓塞手术,就根本不是病!”
嗯?大哥你竟然如此专业!安慰人竟如此粗暴和有效!
心里顿时不觉得自己倒霉了,想:这位先生看上去并不像个文化人,怎么知道这么多?
原来真的是久病成医。
他说起了妻子去年完全没有任何征兆地突然发病,紧急送医发现是脑干部位的动脉瘤破裂,然后昏迷了几十天。
看我一脸懵,他耐心地解释:“脑干和小脑,这两个位置的动脉瘤破裂是相当凶险的,可能因为神经元比较丰富,容易被血浸泡受损。”
后来他妻子终于醒了(醒不了就是植物人),生活渐渐能自理,但是智力只相当于6、7岁的孩子。
他苦笑:“这样的生活,老婆不再像老婆,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我无言,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迅速又说:“不过还有希望,说是还能进一步恢复。”
希望,是一个多么好的东西啊。
很快我就知道什么是6、7岁的孩子了。
男人悄悄告诉我和护工:“你们吃东西,千万不要说吃什么东西,否则她会馋的,家里凡是有的东西都被她找出来吃掉,所以不敢准备现成的食物。”
医生警告:90公斤的体重严重超标,要减重,股动脉穿刺时都找不到血管了。
看那个男人,只像有70公斤的样子,黑瘦黑瘦的。
做完了脑血管造影检查,6小时内有穿刺伤口的右腿不能懂。但是她完全不管那一套,一直在扭来扭去的,还不停地哼哼唧唧:“我难受,我难受”。
其实还不如一个6、7岁孩子的自控力和意识。唉。
男人火速跑去拿片子了,拜托我给看一下。照顾我的护工出去买饭了,我只好下床一直按着她右腿,充当她的临时护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先生没在,她停止了哼唧,看来能分得清里外,然后她就开始给他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这还真像个依赖家长的孩子。
不一会儿,男人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叫着她的小名,跟她开玩笑:“老公不会扔下你跑了的,好不容易娶到手的大胖媳妇哪能不要了!现在我照顾你,等你好了,我老了你要照顾我,不能只顾着跟其他老头去跳舞,把我的轮椅往海里一撅就不管了。”
听了又想笑,又心酸。一个有趣的、苦里找蜜的男人。
女人见到了“家长”,很快又开始哼唧“我难受”,又开始扭来扭去。
我说:“刚才不是表现挺好的吗?也没哼唧。”
他看向她。她嘟囔了一句:“刚才没人听。”
他笑了:“看来就是专门来治我的。”
男人不停地哄,先是用几片饼干诱惑,然后给各种亲戚打电话,报告检查结果很好,给她找个事儿干,消磨一下时间。
先是拨通了他们儿子的电话,是个听上去跟他爸一样有些逗的小伙儿。
他爸说:“你妈可不听话了,要知道这样,就让你来了,就你能管得了她。”
小伙儿在电话那端嘎嘎地笑,言语间完全把她妈当成了孩子,家里共同的孩子。
男人家里是有个小公司的,原本儿子完全不感兴趣,啥都不管,当妈的一病,儿子一夜成人。爸爸照顾妈妈,无暇照管公司,儿子意识到了责任,立刻挑起了公司的担子。
小伙儿比我儿子大两岁。
感慨,感恩,也有点感伤。
父母健康,健在,孩子永远都是任性的。半边天空塌了,孩子只好去奋力顶起来。往往也能行。
一切可做的事做完了,女人闲下来了继续哼唧和扭动,男人似乎耐心到了极限。
我拉着护工出去到走廊上坐着了,想给他们一个空间。自己也想清净一下。
没有人会去指责一个这样的男人收不住脾气的,都是血肉之身,都有忍耐的临界点。
再次回来,女人已经被哄睡了。我们蹑手蹑脚,唯恐吵醒了她。
这样的夫妻。这样的生活。
医护人员
之所以能从心理上接受上次手术一年后再次复发,几天前做造影检查已经穿刺了一次,几天后又需要做第二次介入手术,承受了无数的辐射和造影剂,医院的环境分不开,比如这样的一些病友,比如长发飘飘的姑娘为做开颅手术,剃掉了满头秀发。
参照物不同,感受就不同。
我一口气能数出很多种病,在我的病和那些病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的。可见还不算凶险,只要知道了它的存在。
主任医生站在我的病床前反复向我解释为什么需要二次治疗。总之,绝不可能是医生的治疗方案有问题,而是患者的身体情况不同,愈合能力不同。
然后又仔细解释,为什么这第二次手续中,预先制定的方案没有完全得到实施,也是受到我的脑血管情况所限。结果是:放进去的支架因为空间不够打不开,因此只好又取了出来,由于不能回收,3万多的材料费需要病人支付(医保报销后也要付左右)。
我请他坐下来讲,他坚持要站着,几乎是给我普及了一课时的“神经外科必修课”,其实我已经在他拿给我的“知情书”上签字了,医院产生什么医疗纠纷。
放不了支架也有好处的,就这样吧。
我知道他是在进行医患沟通,比较耐心的那种,至少是让我觉得。
也算够诚意了。
医护人员的态度,有时候是重要的。
比如有的护士显得对病人充满同情心和关心,会记得病人的名字,而不是只是X床,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矛盾或病人要求过高,撒个娇、开个玩笑,病人或家属会较少苛责。
而有的一直板着脸,眼睛里冷冰冰的,很少会跟病人对视。也许是性格所致,也许是生活都不易。
只要不出错,就是合格的医护人员,医院不是服务行业,不能要求微笑服务。
但是这样“公事公办”的医护人员,一旦与病人发生矛盾,就不太容易化解,很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有个病友说,手术前躺在手术室里准备全麻,忽然觉得有些伤感,眼泪流了下来,有点呜咽。
麻醉师冷冷地说:“别哭了!你要再哭,就不能进行麻醉了,手术也不能做了!”
没有同情,没有安慰,彼时倒也是合适的,否则很可能越安慰越哭得厉害。有些路,毕竟只能一个人走,脆弱的时刻挺一挺就过去了。
医护人员的同情心大概也早就被日复一日的工作透支了。
不知道医护人员的专业性里面,是否包含让病人感受到一定的同情心?
交流病情时,高级别的医生说话很严谨,不会为了让病人心理上更容易接受手术方案而给病人虚妄的承诺。这是专业的表现,与是否人性化无关。
而有的医生会过度安慰或过度承诺,尽管是出于好意,但一旦手术结果不理想时,很容易产生纠纷。
凭我有限的医疗常识,知道我经历的毫无疑问不是医疗事故,医院的创收手段,医院还是有这个信任的。
也许是治疗手段的局限性,即使是医生本人的经验局限,那也是我的选择。医学并不是万能的,病人也并不总是能被治愈的。如果每次都要求万无一失,医学是不可能发展的,被治愈的病人会更少。
毕竟我顺利度过了第二次手术,慢慢地又可以活蹦乱跳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已经损失的,就不去想了。
但是假如明年复查还有问题,我将决定不再继续信任该院的治疗水平,会医院和医生去碰碰运气。
出院后,医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