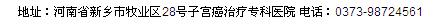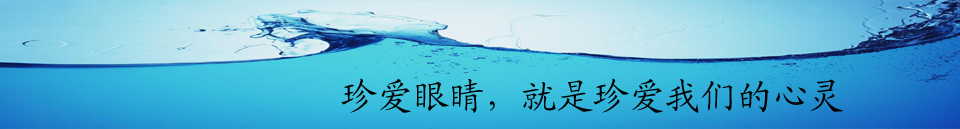
亲眼目睹老公死在我面前,我不仅没哭,反而
我与潘国强是中学同窗,后来我进入医学院,他选择了会计专业。我们毕业后回到了县城,医院工作,他则加入了粮食局。因为同为镇里出来的同学,后来又在同一个县工作,我们的交情自然比普通同事更为深厚。
相处数年后,我们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原因简单,熟悉而信任,觉得与其与陌生人结合,还不如我们两人共同度过人生。况且,我容貌普通,能力一般;潘国伟身材矮小,相貌显老,作为基层小会计,也并非是其他女人的理想对象。
婚后的日子过得幸福。虽然我们之间缺乏浓烈的爱情,但家庭生活和谐美满。
潘国强的工作是朝九晚五,医院的工作时间则更为漫长,每三天还需要值夜班。因此,家务几乎都由潘国强负责,包括搞卫生、烹饪和洗衣服。他默默地承担这一切,毫不抱怨。
每当轮到我值夜班时,潘国强都医院,等我吃完后再独自回家,将餐具洗刷得干干净净。医院女同事羡慕的焦点。
我知道潘国强爱喝酒,家里常备几瓶酒,他在用餐时总喜欢来上两杯,他称之为“小酒怡情”。酒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一种解压的角色,尤其是在会计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他会借助酒来缓解疲劳。
有时我也会试图劝阻,但考虑到他的工作特点,我并不过多干涉,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释压方式。
随着女儿的出生,潘国强更加欢欣鼓舞,酒量逐渐增加到每天四两,酒瘾也逐渐升级。然而,那时的他年轻,新陈代谢快,整个人看起来并无大碍,我也没有太过在意。
女儿两岁那年,我和潘国强的事业都迎来了一次飞跃,他成为单位的主办会计,我获得了科室的中级职称。前景看似光明无比。
然而,生活却突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故,将我们的生活推入了深渊。
那年女儿年仅四岁,全国粮食系统展开一场自上而下的审查。令人意外的是,这次审查揭露了潘国强所在单位存在的一项巨大的金融问题,数百万元的款项不翼而飞。
数百万元在当时或许不算什么,但对于90年代末依然贫困的县城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潘国强不幸成为这场事故的替罪羊,最终锒铛入狱。两年后,他才获得释放回到家中。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出狱后的潘国强重新回到了原单位,尽管职务已从主办会计沦为最低级的出纳。
在那两年的监禁中,潘国强究竟经历了什么,他始终保持沉默。然而,我明显感觉到他变得与以往不同,性格变得乖张而暴戾,对酒的依赖也日益加深。
每天早晨醒来,他第一件事就是倒一杯酒,只有这样才能振作精神去应对其他事务;吃饭时必定伴随着酒,上班时杯中所装并非清水,而是酒;每天晚上入睡前,他都会在床头倒上一杯酒,以备半夜醒来时的消遣。
随着酒量的增加,他变得越发糊涂。
接孩子时竟然走错了学校;带孩子外出竟然弄丢了;骑车时不慎掉入排水沟;做饭时竟然放了油却忘了放菜,差点引发火灾。
他的谎言也是不绝于口。
告诉我晚上要加班,却在半夜接到朋友电话,得知他其实并没有加班,而是躲在外面喝了一个晚上的酒。
尽管我曾苦口婆心,医院试图强行戒酒,但效果甚微。只要有一点空隙,他就会将自己沉浸在酒海之中。
一年后,我也感到力不从心,不再劝说。然而,每当接到朋友的电话,我仍然会去接他回家,这或许是作为妻子的责任吧。
离婚从未是我的考虑。
潘国强虽然沉迷于酗酒,但酒后并没有家暴行为,也没有其他恶习。再加上孩子尚幼,而他的年收入依然可观,足以承担大部分家庭开支。因此,我只能将就着过,抱着聊胜于无的心态。
也许因为我年轻,曾经完全忽略了潘国强的行为对孩子产生的巨大影响。我没想到,曾经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变成了现实。
特别是对于女儿来说,她曾经和潘国强关系亲近,但现在每次看到爸爸喝得两眼通红、喘着粗气,她就感到害怕。生怕说错一句话或者做错一件事,潘国强就会向她扑上去。她甚至不愿意再和潘国强一起外出,担心被同学嘲笑和瞧不起。
这种变化潘国强怎么能够不察觉呢?
他开始恶语相向,痛骂女儿是白眼狼,喝醉后还非得跑到女儿学校门口,在同学面前指责女儿不孝顺。这让女儿对他更加反感。
即使上了中学,女儿看到潘国强喝醉晕倒在小区里,也是目不斜视地走过去。
除了女儿,我也渐渐成了潘国强的发泄对象。
他说我没有教好女儿,说我不管他,甚至巴不得他死在外面。
我又能怎么样呢?我知道他心里苦,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家人和单位的理解。有时他甚至觉得是我把他推向了深渊。如果当初我没有要求他努力一点,争取做个小领导,他就不会受那两年的牢狱之苦,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波折。我尽管解释过,但如今的他整日沉迷在酒精的麻痹里,听不进我们说的一句话,更不会敞开心扉。我只能听之任之,这反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让潘国强对我充满了怨恨。
白天在路上碰到我,不管周围有没有人,他都会指着我的鼻子骂;晚上,喝得醉醺醺的他回到家,不管几点,必定要把全家人闹起来,轮流地骂上一番。
家里的家具已经被他折腾得重新换过几次了。到最后,我也死心了,除了吃饭的家伙,什么都不要了,任由客厅里空荡荡的。
邻居也找过我很多次,要我劝劝潘国强,不要在半夜闹腾。没想到,这反而激怒了潘国强,将邻居堵在家门口一阵痛骂:“我自己的家,为什么不能闹?关你什么事?”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邻居敢说他半句不是了。
一天半夜,我接到“嫂子,医院来吧,医院了!”
医院,潘国强已经被推进了急救室,正在洗胃。这一次,潘国强竟然喝成了胃出血,还接连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潘国强终于醒悟了,决定重新振作起来。
他确实也收敛了一些,但只维持了半年的时间。
半年后,故态萌发,又开始喝起酒来,并且变本加厉了。
单位也实在忍受不了他了,在他四十岁那年,含蓄地给他提出了早退的要求,潘国强欣然接受了。
有钱有时间的潘国强一发不可收拾。
我早上出门上班,他也出门,去餐馆里呆着,从早上一直喝到人家打烊。
家里,除了是他偶尔回来睡觉的地方,其余什么也不是。
潘国强深陷酒精的泥沼,导致大脑皮层缺氧,影响脑部供血和神经,口齿不清、行动不协调,陷入废人的境地。作为他的妻子,我承担起了巨大的责任,独自负责送女儿上学、照顾家中的老人,而公公婆婆虽有歉意,却无法管束他们的儿子,只能将期望寄托在我身上。父亲曾多次劝我离婚,但我犹豫不决。
眼前的现实是,潘国强每次醉酒都使家庭陷入混乱,然而,女儿选择了艺术专业,学费和补习费让我难以独自承担。因此,即使家里空荡荡,我仍然忍受着这一切,将潘国强的工资视为分担生活负担的一种方式。
一天,潘国强又一次酩酊大醉,倒在单元门口。邻居好心通知我,但当我伸手搀扶他时,他竟然挥手打在我脸上,让我眼冒金星。虽然我认为是无意的,我还是强忍痛将他弄回家。然而,他睁开眼睛,盯着我,恶狠狠地说:“不是说了让你……”接着,他扑过来,将我撞倒在地,数次拳打脚踢,声称是因为我导致他坐牢。
在邻居们的注视下,我试图推开他,但他的力量太大。女儿听到声音赶了出来,也被卷入混战。物业的介入才制止了他的暴力行为,但我和女儿都已经受伤。
第二天早上,潘国强跪在我们面前,涕泪交加地表示歉意,声称无法控制自己。我看着女儿,她愤怒的表情让我陷入犹豫。是否应该原谅他,成了我难以抉择的问题。
潘国强的变化并非一次殴打的结果,他似乎在某次暴力中找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满足感。曾经酒醉后即刻进入梦乡的他,如今却在家中肆意嘈杂,时而疯狂咆哮。
只需我走近他,立刻面对的就是他的拳头。女儿也无法幸免。
为了保护女儿,我决定安排她住在学校,自己成了潘国强唯一的目标。
这时,我仍未考虑离婚,确实,那时还未想过。
我一直相信潘国强的人品并不坏,期待有一天他会觉悟,我们家的困境也会结束。
然而,我太天真了。一旦染上了瘾,改变并非易事。
那一年,我遭受了他五次的殴打,脸部肿胀,鼻子断裂,甚至肋骨折断。
我逐渐失去了最初的信心,也不再期待他会改变。甚至,我开始憎恨他,深入骨髓。
每次回到家,我都将自己锁在房间里,用桌子顶住门,不论他在外面怎么大声嚷嚷,我决不开门;第二天,趁他还在沉睡中,我早早地溜出去。
即使有朋友电话叫我去接人,我也不予理会,无论他在外面是死是活。
我曾找过他的单位,但单位回复称这是家事,他们不便干涉;我还找过妇联,妇联调解过几次,但之后依然我行我素。提出离婚,潘国强根本不当回事,也不愿意出面;在第六次家暴之后,我终于踏上了法律诉讼的道路。
法律诉讼充满曲折,最为棘手的是需要等待3-6个月的时间。
我一边保护自己,一边耐心等待离婚的终局。
一个半月后的一天,凌晨三点,电话响起。
我朦胧地接起“嫂子,我是小张……”
小张,潘国强的酒友之一。一听到他的自我介绍,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重新躺回床上。
我知道他是让我去接人的,但我不愿与这样的人扯上关系,凭什么要我去接他?接回来还要被打一顿吗?
五点,家门被敲响。
我打开门,物业人员站在门外。
“姐,出事了。”
我随着物业到小区一角,看到潘国强,随后也赶到了。
不断为他进行心脏按压,嘴鼻间流出深红的血液。大约30分钟后,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定定地望着我,不到一分钟,眼神渐渐黯淡,呼吸停止了。
离开后,殡仪馆的人还未到,物业问我是否要把他抬回家,我无表情地看着他,沉默了很久,最终摇了摇头。
潘国强因酗酒导致胃出血,失血过多引发心脏骤停。
我没有通知女儿,独自跟随殡仪馆离开。
完成了一系列电话,先是给我爸爸,然后是公公婆婆,接着是朋友,最后是他的单位和我的单位。
心情纷乱,嘴上说着不在乎他死活,但看着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心里还是乱成一团。
然而,我没有哭,眼泪无法流出。
三天的追悼会我一个人操办,全程未曾合眼,没有一滴泪水。
这是我对他最后的尽责。
逝者已去,生活依然在继续。
我重拾了过去的生活,适应得相当迅速,感觉生活中少了他并没有太多改变,女儿似乎也没有感到太多不适。
一天,我和女儿坐在沙发上,晒着温暖的阳光,享受着水果,女儿突然说了一句:“妈妈,我觉得现在这样的生活挺好的,很轻松。”
我陡然意识到,轻松,没错,就是轻松。
我不再为一个人挂念,不再为一个人顾虑,也不再时刻提防要保护自己。
这种感觉,就是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