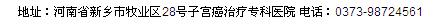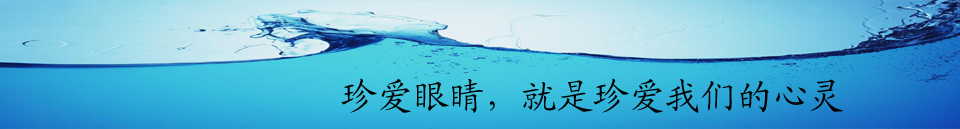
你是罪人长夜有时尽连载二
《长夜有时尽》
连载二
你对我三分恨,我会用七分深爱,还给你
你对我三分好,我会用七分疼惜,还给你
内容/作者简介①《长夜有时尽》内容简介:
——你对我三分恨,我会用七分深爱,还给你。
——你对我三分好,我会用七分疼惜,还给你。
九岁那年,画扇进了祁家。连年的哥哥收养她当女儿,按辈分,她该叫他小叔叔的。
他比她大了七岁,从十六岁开始,渗透进她的生活里——
她父母死于车祸,所以怕过马路,没关系,他带着她。
她被人挤兑陷害,他是小叔叔,理应护着她。
……
在她痛失父母的阴霾时光里,在她渐渐长成曼妙少女的那些年华里,他一直在她身边。
可是九年后,已成国际名模的他,却向全世界宣布:我要结婚了。
新娘不是她。
她喜欢他整整九年,他却要和别人结婚了。他对她的误解怨恨,越积越多,越来越深。
“你送我什么,我就还你什么。”画扇看着连年,平静地开口。
“嗯?”他狭长漂亮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疑惑。
“八月十七日,黄道吉日,结婚的,不止你们一家。”画扇的神色依旧平静。
他因她背井离乡,她为他相思成狂。九年的时光,磨灭不掉他对她的恨,却也消弭不了她对他的爱。
②《长夜有时尽》作者简介:
然澈
89年重阳节生,中文系硕士。
已出版长篇小说《南心不负》、《终于等到遇见你》、《弦音》等。
爱萌物,爱猫狗,日本神魔动漫控。
我有好故事,讲给你来听;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很高兴和你相逢。
新浪微博:
然澈cheers图书11月份上市连勇心口猛地跳动几下,他又折回画扇的床边,宽厚的手掌抚着她头顶柔软的发心,画扇扑闪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问他:“他们……再也不会来看画儿了,对吗?”
连勇心头一酸,点了点头。
画扇咬咬嘴唇,又问:“他们,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了,是不是?”
看着眼前这个九岁的孩子分明悲伤,神情也无措极了,却执拗着不肯落泪的模样,连勇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涩,他伸过手去揽了揽画扇小小的身子,一下一下抚着她的背脊,却不知如何开口。
画扇见勇叔叔不说话,就知道自己又问蠢问题了,她把尖尖的小下巴支在连勇的肩膀上,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一会儿便濡湿了连勇肩头的衣裳。连勇舌尖发苦,他是医生,救死扶伤义不容辞,却无法医治一个孩子的心伤。
安静了好久好久之后,画扇抬起稚嫩的一张小脸,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盈满了哀求:“画儿乖乖的,画儿会听话的,勇叔叔不要赶我走……好吗?”
这一句话,加上纯粹是孩童哀求的神色与语气,让连勇心头那根埋入血肉不敢见人的刺越发深入了,深深的内疚与负罪感,霎时弥漫了他整个心脏。
“好。”他抱紧画扇的小身子,眼底笼上一层雾气,信誓旦旦地保证,“不赶你走,叔叔把你养大,送你上学……绝不赶你走……”
2.
从洗手间里出来,画扇的眼睛红红的。台上聚光灯下的祁连年笑容得体地回答在场记者的各种疑问,目不斜视,臂弯里挽着巧笑倩兮的Lisa,一个玉树临风,一个风姿绰约,两人般配得宛若金童玉女。
画扇坐下去时,陆齐安意味深长地朝她看过来一眼,没多说什么,只简单地告诉了她一个日期:“八月十七号。”
画扇的心脏一抽,隐隐地发疼,她下意识地抬眼朝台上看去,恰好看到连年对着镜头浅笑着亲吻Lisa的脸颊,那场面亲昵得近乎残忍。
现在是七月,下个月的十七号,他们……就要结婚了吗?
四周的人在低低交谈着,所有人都在说台上那一对男女是如何的般配,画扇觉得再坐在这里再听下去,自己一定会窒息的。
就在她准备起身的时候,陆齐安的一只手伸过来,摁在了她的手背上。画扇抬眼,就见到他冷冷的眼神里裹着怒气,可是她管不了那么多,抿抿唇,利落地起身:“我去透透——”“气”字还没说出口,却因动作过大,佩戴在胸前的那朵木棉花形状的银质项链勾住了餐布,带得桌上的东西哗啦啦撒落在地。
因动静太大,所有人都朝这里看了过来,陆齐安优雅地起身,不着痕迹地把画扇摁在座位上,成功地将众人或探究或埋怨的视线都引到自己身上,继而对众人报以歉意的微笑。
画扇被摁下去时,下意识地朝台上看了一眼,就连站在连年身边的Lisa都闻声朝这里看过来了,他依旧浅笑着对着镜头,对这边的动静恍若未闻。
画扇忽然间就觉得沮丧极了。她觉得自己像个小丑,而且是全世界最最可悲的小丑,因为她没有观众——无论她做何表情,无论她是哭是笑,她最最在意的那个人,始终都不曾朝她投过来一瞥。
服务生很快就把撒落的东西收拾好了,陆齐安坐下来,他墨色的眸子里带着几分不赞同,淡淡地看了画扇一眼。
画扇揪紧裙子,现场的秩序已然恢复正常,所有人重新开始言笑晏晏,她咬了好久的嘴唇,才憋出低低的一句:“我们……走吧。”
陆齐安看她一眼,又看了看在场的几位商业巨头,中途退场虽说不好,但是画扇的脸色白得让他恼火,更……心疼。
“好。”他握住她的手,侧身对身边一位朋友说了句什么,然后朝台上看过去,恰好祁连年也朝这里看过来。他低头拥着画扇,几乎把她半个身子抱在怀里,“走。”
画扇听不见他的声音,脚下无意识地走着,她自走进这个华丽的会场整颗心就一直系在那个昔日对她呵护备至的男人身上,可是,她却连在离开时回头再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唯恐看到他冷漠的表情。
画扇没有回头,所以她没有看到连年一直目送她的背影,那张清俊的脸上,再没了方才那么张扬的表情,反而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从大厅里出来,外面居然下雨了。
陆齐安把车子开过来,就看到画扇神情恍惚地站在路边,他叹了口气,朝她伸手:“快上车!”
画扇终于回神,怔怔地朝他看去,却忽地抱住了自己的胳膊,警惕地往后退:“我不回家!”
陆齐安黑眸微眯,隔着雨帘静静地看着画扇:“今天父亲生日,说好了回去为他庆生的。”
画扇红着眼睛反驳:“那是你爸爸,不是我的,要回去你自己回去!”
陆齐安眸底的戾气被激了起来,他霍地打开车门,也不顾外面雨若瓢泼,大步朝台阶上的画扇走过去,拉住她的胳膊就要强行带她走。
画扇挣扎,陆齐安抱住她的腰,恶狠狠地在她耳边说:“他已经对全世界宣布要结婚了,你以为还改得了吗?告诉你,只要有我陆齐安在,这场婚礼谁都别想破坏!”
最后,画扇还是被陆齐安抱上了车,她哭得眼泪混着雨水分不清,眼睛酸涩得和心脏一样疼。陆齐安踩油门的那一秒,画扇不死心地朝车窗外看了一眼,然后她的身子一僵。
惊鸿一瞥之间,画扇看到,酒店门前的柱子旁,赫然立着一抹颀长的身影,那抹身影,画扇认错了谁都绝不会认错了他。
连年,是连年!
画扇急急喊道:“停、停车,停车!”
陆齐安哪里肯听,画扇渐渐哽咽得不成字句,脖子扭着,近乎执拗地看着那个已然彻底消失在身后的身影。下一秒,她恍若梦醒,伸手就要抓车内的门把手,却被陆齐安腾出的一只手先一步控制住了。她挣扎,陆齐安身子微微侧过来一点,抓紧她,就在她试图拼尽力气挣开他时,车身骤然一震,画扇的脑袋一下子就磕在了车窗上,下一秒,是轮胎擦过地面留下的刺耳的紧急刹车声。
“该死!”陆齐安低低咒骂,他被画扇分了神,又是雨天,居然和迎面的车撞上了。
陆齐安看了一眼画扇,见她揉着额头,并无大碍,这才阴沉着脸斟酌着用不用下车处理这起车祸事件。
他才打开车门,画扇身边的车窗突然被什么尖锐的物体猛地击碎,一柄清亮的匕首即时伸进来抵在她的颈间。
那柄匕首在雨夜里闪着寒光,陆齐安的身子顿时僵住,他不敢妄动,凝眸屏气,眼底的戾气一点一点地加深。握着匕首的那人微微倾下身子,露出带了一道伤疤的一张脸来,他浑身已经被大雨淋湿,看不出已经在这里等了多久。
“陆少爷,您不认识我吗?我是阿乐,我兄弟被您的手下砍得不能动弹,劳驾您去看看他吧。”
陆齐安沉默了片刻,终于阴沉着脸出声,他盯着阿乐的眼睛:“放开她。”
阿乐很聪明:“她是你的小情人,你当我傻啊?别废话,下车!”
陆齐安眼底的戾气越来越浓,很明显,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他看了一眼画扇,画扇闭着眼,眼睫毛乱颤,显然是害怕得紧。他刚动一动,就被阿乐发现,立刻引来一声厉喝:“磨蹭什么!快下车!东子,去拉他下来!”
叫东子的人听了指示,伸手要来拉他,却被陆齐安一脚踹在肚子上:“滚!”
这边阿乐已经把画扇从车里弄了出来,匕首仍抵在她的脖子上,他手臂一动,画扇惨叫了一声,匕首在她脖子上划开一道口子,鲜血立马就冒了出来。
陆齐安的眼睛立刻就红了,他刚想朝前扑过去,阿乐就狞笑了起来,他把匕首往上挪了一点,手臂箍着画扇的身子,匕首紧贴着她的脸:“不想她毁容就老实点儿!”他指了指自己那辆车,“快钻进去!”
陆齐安看向画扇,画扇眼睫乱颤,无措地看着他,陆齐安的嘴唇抿成了一个无比僵硬的弧度。
东子立刻凑上来,手脚麻利地用绳子绑住了陆齐安的两只手,阿乐也赶紧带画扇上了车。车子发动,激起一地水花,朝东飞速而去。
“嘿!”
东子突然用力拍了一下方向盘,侧脸对坐在后座依旧用匕首抵着画扇脖子的阿乐说:“前头的路被警队封了!”
阿乐愣了一下:“掉头!”
掉头走了没多久,道路被封的事情再次上演,阿乐用匕首指着陆齐安的脸:“你敢玩阴的?!”
陆齐安冷笑道:“那你早就没命了。”
“你……”
“乐哥!”东子打断阿乐的话,“警车好像开过来了!”
阿乐看了眼后视镜,果然有警车开近。他脸上那道伤疤霎时变得狰狞起来:“放了他也太便宜他了!”
话没说完,他手里的匕首已经朝陆齐安的腹部捅去,陆齐安侧了侧身子,车内空间狭小避不开,刀尖划过他的胳膊,拉出一道深深的口子,血立刻汩汩地涌出来。
警笛声让阿乐慌了神,陆齐安当机立断,用肩膀撞过去,阿乐不防,手中的匕首被撞得掉到座位下面。眼看警车就要追上来,他这才弃了车,和东子下车跑了。
陆齐安胳膊上的血越流越凶,阿乐那一刀刚好伤到了他的动脉,画扇吓得惨白了一张脸,她下车疯了似的对着警车挥手,等到警察赶过来时,陆齐安的意识已经渐渐不清。
画扇万万没料到,自己居然会在警车里看见祁连年。他垂着眼睫,陆齐安被抬上警车时,他瞥了一眼跟在后面的脸色惨白浑身湿透的画扇。
和祁连年一起的,还有他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刑警大队队长的儿子,许远。
许远看见画扇脖子上的血,脸一黑:“哪个兔崽子欺负我家小扇子,别让老子抓着他!”
车开得很快,医院,陆齐安被送进了病房,画扇脖子上的伤口也由护士包扎了一下。许远看画扇没什么大碍,就要走,他如今是警察,这个绑架案是他第一时间去的现场,他得去处理。
连年也要起身,画扇的脸一下子更白了:“哥……哥哥……”
比起刚才那声“小叔叔”,画扇这声“哥哥”直击连年心底,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连年表情僵硬,但到底是在聚光灯下讨生活的人,最擅长的就是表演,只是经过很短暂的一秒,下一秒他就恢复了自然。
连年没有看画扇,对许远说了一句“走了”,就要往外走。
“哎哎。”许远喊住他,“你不能走啊!”
“我还开着发布会。”急躁地扔下这句类似解释的话,连年便没有再停留。
许远盯着他的背影看了好一会儿,才回过头来,他盯着画扇的眼睛说:“是他报的警。”
画扇呆了一下,许远又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你放心,他要娶别人,我绝不赞成。不只他今天发布会我不去,就是大婚那天……”说到这里,许远忽然自己停顿了一下,“不,你放心,他绝不可能娶姚悦的!”
画扇还没来得及说话,许远站起身来,凑近过来抱了抱画扇的身子,飞快地说了一句:“不管他还是不是祁连年,我都还是你远哥哥。小扇子,以往那些事儿……不怪你。早晚有一天,连年会想通的!”
说完这些,许远轻轻拍了拍画扇的肩。
画扇安静了好久好久,医院里不时有护士医生或者病人经过,却都进不了画扇的视线里。她揪扯着佩戴在胸前的那个木棉花形状的项链,指骨泛白,纤弱的青筋恨不得从肌肤里爆裂出来。
远哥哥说,不怪她……不怪她……真的不怪她吗?
如果不是因为她,祁家就不会被打乱了平静,如果不是因为她,太多太多的人都不会受到牵累。
远哥哥说,连年会想通的。
会……会吗?
他曾经用那么怨恨的眼神看着她,他曾经冷冰冰地对她说:“你是罪人”。对她如此痛恨的他……真的会原谅她吗?
3.
画扇靠着墙壁,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梦到了自己的小时候,梦到了,他们久违了的昔日时光。
连年和画扇一起上学的第一天,连勇交代了很多事,他知道自己的弟弟毛毛躁躁的,所以不甚放心,一直跟在两人后面嘱咐了很久,唠医院里寡言少语的祁大医生了。
连年懒得听哥哥絮絮叨叨,他拽住画扇的小胳膊,大步就往门外跑,直到出了小区,才松开了她的小手。
侧过脸,连年就看见画扇一脸的戒备神色,少年的意气顿时就涌上来了。
她不愿自己碰她是吗?那他偏要碰。
连年伸手痞里痞气地去摸画扇的小脸,画扇恍若惊弓之鸟地往后避,连年步步紧逼,嘴上还气呼呼地说着:“喂,我长得是有多凶恶啊,你至于这么怕我吗?大哥抱你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副德行?”
画扇小脸苍白嘴唇紧抿,什么都不说,只受了惊似的往后避,忽然,胳膊被眼前这个少年拽住了。连年好看的眉眼里盈满了怒气,恶狠狠地瞪她:“退到墙角了!你可别磕着,磕着了大哥就该收拾我了!”
连年要送画扇去新学校上课,虽然从家里出发足够早了,但毕竟还是经不起这样磨耗,眼看画扇对他防备得很厉害,他看着她的小脸,裹着怒气冷哼了一声,回身先走一步:“快走吧!”
连勇交代过了,画扇怕车,而且家里离学校不远,所以这一段时间里,连年和她都步行去学校,不坐车了。
连年其实没什么不满,他上学从来都是骑单车去的,如今有机会走走也不错。只不过,看着落在自己身后一步开外的画扇,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喂。”
画扇脚步顿住,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抬起来,看着连年,不说话。
“你走快点儿行不行?”
画扇沉默,然后举步,步子明显比刚才大了一些。小小的瘦弱的身子,大大的步伐,很怪异的感觉。
又走了几步,连年再次发难:“你都不说话的吗?那去学校了怎么跟同学们玩?”
画扇又顿住了脚步,这次连眼睛都不看连年了,依旧不说话。
连年恼得不轻,却也无可奈何,冷哼了一声就别过脸去。
接下来的路程,就在两两沉默中度过了。连年生性好玩,闲不住,走了几步看见前头木棉树上的花开了,轻盈地跃了一下,就摘下一朵花来。
他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回身就要递给画扇,回过头去,却见她像是痴傻了一样愣在原地。
她那双像是能看到人心底去的大眼睛,就那么死死地盯着少年手里的那朵花。
连年先是怔了一下,回过神来他把花递过去:“喏,拿着。”
画扇却钉在当地了似的,依旧死死地盯着连年手里的木棉花,不说话,也不伸手去接。
连年的手僵在了半空中,下一秒,素来被当成王子追捧的英俊少年脾气就上来了,他修长的手指微微一握,一把将手里的花朵捏得凌乱不堪,然后甩在地上,转身走了。
身后,一直盯着木棉花看的画扇,眼眶却红了。
木棉……妈妈,这里也有木棉花……
在画扇的记忆里,妈妈最爱的就是木棉,从小到大,画扇所有的衣服上几乎都有木棉形状的佩饰。她曾经不解地仰着小脸问妈妈,当时妈妈站在偌大的落地窗前,她回过身来,浑身笼罩在明媚旖旎的阳光下,染上了一层温暖的光华:“因为……木棉好看啊。”她朝画扇走过来,蹲下身去,微笑着抚摸她前额的头发:“妈妈爱木棉,就像爱画儿一样。你也要快快长大,长大了的画儿,一定比木棉花还要好看呢。”
画扇揪着裙角,妈妈,你最爱的木棉在这里,可是,你在哪儿呢……
连勇之前已经给校长和老师打过招呼了,连年把画扇交到老师手里,准备去自己学校。
走了几步,他没来由地回了一下头,居然看见画扇还没走,就站在教室门口,用那双黑白分明的澄澈眸子,一眨也不眨地看着他。
连年这下心情好了,他也不急着回去上课了,优哉游哉地踱回到画扇的身边,微微低下身子,不无得意地说:“怎么,害怕了?还是,舍不得我了?”
连年俯低了身子,距离画扇的脸极近,少年清新的呼吸就那么扑面而来,直直扑到了画扇绷紧了的苍白小脸上,甚至,连年看到画扇的睫毛都跟着他的呼吸颤抖了起来。画扇别开脸,不与连年对视,小手却在书包里摸索起来,好一会儿,手递到连年的面前,掌心里,居然是一块金凤呈祥的蛋糕。
连年怔了一下,好看的眉毛一挑,问画扇:“给我的?”
画扇也不说话,似乎踟蹰了好久,才终于做出一个动作——她试探着拉过连年的手,展开他的手掌,把蛋糕放到他掌心上面,然后扭头进教室了。
连年愣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笑开了,那个小东西,也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不知好歹嘛。
一放学,连年慢悠悠地收拾书包,许远问他是回家还是去哪儿玩,连年说:“去附小。”
许远没听清,抓起书包就跟了上来:“去见谁,去见谁,带上我呗!”
连年想了想,带上就带上,反正那丫头也是个小哑巴,在谁面前都不说话的。
到了附小,许远就愣了:“我说祁连年,你不会是……有私生子了吧?”
连年痞痞地勾起嘴角,眼角眉梢都挂满了得意:“不是私生子,是私生女。”
他俩正在这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画扇的小身影出现了。她依旧是来时的那身装束,但连年一眼就看出她的样子和早上来时不一样了。
等到走得近一些,画扇一抬眼,看见连年了,当然也看见连年身边还站着一个陌生的大哥哥,就顿住脚步,不肯走了。
连年走上前去,许远也跟过去,画扇赶紧抱紧书包,神色像无措的小兽,企图挡住什么。
连年更加狐疑了。
他伸手去扯画扇怀里的小书包,画扇往后退,他往前,她再退。
连年本来就没什么耐心,一下子恼了,他指挥许远:“抓住她的身子!”
许远摩拳擦掌地就要伸手抓画扇的胳膊,画扇眼看避不开,慢慢红了眼眶,她咬了咬嘴唇,似乎很是为难了一下,然后一伸手,赶在连年抓住她怀里的书包的前一秒,把书包给扔了。
这下,连年和许远齐齐呆住了。
——画扇身上那件小小的雪白公主裙,裙身位置涂满了黑乎乎的一层染料,她本就个子矮小,那块黑乎乎的颜色衬着白色的裙子底色,愈发显得触目惊心了。
是连年先反应过来,少年两道好看的眉毛霎时就蹙起来了,他盯着画扇的脸,语气低沉地问:“谁欺负你了?”
画扇咬嘴唇,低垂着眼睫,不说话。
许远在一旁帮腔:“小妹妹,告诉哥哥,你说是谁欺负你了,我帮你去揍他!”
一听这话,连年似笑非笑地看了许远一眼,小妹妹?他挑着嘴角,嘴唇动了动,却没说话。
许远明明是想帮她,但画扇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依旧含着戒备,自从连年见她第一眼她就是这副模样,所以连年并不惊诧,但是许远就不同了。
许远是出了名的没心没肺,和画扇四目相对,看清她眸底的警戒和疏远,不由得身子一颤。
他朝连年看过去,连年笑着哼了一声:“除了我哥,她和谁都不说话,对我还不冷不热的,对你能好到哪儿去?”
许远不服了,栗色的短发映着徐徐落下的夕阳余晖,显得煞是执拗,他事先也不说,径直弯下腰就去抱画扇的身子:“你不说是吧?好,我抱着你去,你给我指指那个坏蛋坐哪个位子。”
许远的老爸不愧是做刑警的,就连他的“拷问”能力都不错。
他三言两语就从画扇嘴里哄出话来了,栗色的头发映着夕阳变得金灿灿的,他勾着嘴角笑了笑,回头朝连年看过来一眼,掩不住一脸得意。
然后,他把画扇放下,大步朝画扇刚刚指的那个位子走了过去。
出了教室,连年不无嘲讽地看了看许远的脸:“你爸要是知道你在小学生的身上做这么让人不齿的事,怕是饶不了你吧?”
许远摆摆手,满不在乎地笑:“说那么难听干吗,不就是把他凳子腿儿弄折了吗?我小时候还往同桌帽子里塞小蛇呢,够便宜他的了!”
到了路口,许远和连年他们不顺路,要分开了,他看了看垂着小脑袋的画扇,朝连年问:“咱妹妹叫什么?”
连年冷哼:“她是我侄女。”然后又加了一句,“程画扇。”
许远的脸色顿时就五彩缤纷起来了。
连年正得意,许远却敛了脸上的尴尬表情,伸过手去亲昵地揉了揉画扇的脑袋,用一种大哥哥宠溺小妹妹的语气说:“好名字。”
然后他拍拍她的脑袋:“走了啊,小扇子。”
那天回家的一路上,连年都在阴阳怪气地嘀咕着“小扇子”三个字,到了连勇的家,一推门,居然看见沈碧玉大大方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副等人的样子。
连年有点儿愣怔:“妈,你怎么……来了?”
后俩字他没问出口,坐在沙发上的沈碧玉目光径直跳过自己的儿子,看向正躲在连年身后的画扇,语气倨傲地说:“你哥今晚有一个大手术,他打电话求我来帮他看一晚上孩子。”
一听这话,连年还没来得及说话,身后的画扇身子就是一僵。
祁妈妈对自己很不友善,画扇自然知道,她没想到祁连勇会托付她来照顾自己。她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想说“不用管我,我自己没事的”,医院太平间里哭得太过歇斯底里以至几乎失声之后,多日来她尽量少说话,甚至连话都不怎么会说了。
沈碧玉从沙发上起身,吩咐连年:“打电话叫外卖吧,今晚我不想做饭。”
连年看了沈碧玉一眼,然后侧脸看了一下垂着脑袋的画扇,有些欲言又止地喊了沈碧玉一声:“妈……”
沈碧玉保养甚好的面庞上浮起一层不悦,她盯着画扇裙子上那块大大的污渍,没好气地说:“怎么,我都屈尊来这儿做保姆了,你倒还不愿意?”
这句话,她不是对自己儿子说的,锐利的目光嗖嗖地,直直朝神情颓丧的画扇射过去。
连年心想妈既然肯来替大哥照顾画扇,就说明她开始渐渐地接纳她了,哪敢再让画扇把她激怒,忙不迭地揪住画扇的胳膊,一边对沈碧玉说“我们去放书包”,一边推着画扇往卧室走。
直到走到了卧室门口,连年才反应过来,这一次,画扇居然没抗拒他碰她。
吃饭的时候,画扇安静得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她默默地扒饭,明明吃不了多少,却也没敢像以前在家里那样任性地把不喜欢吃的菜夹到爸爸妈妈碗里,安静得跟只小猫似的。
吃过晚饭,沈碧玉催连年回家,连年一个月以后有场小考。
可连年赖着不想走,画扇更是莫名其妙地怕他真走了,也不说话,只拿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不时朝连年身上看一下。
连年和画扇四目相对,见她眸底隐隐有那么一丝畏惧之色潜伏着,不由得意起来,怎么样,这个时候知道他祁连年的好了吧?
他走过去,对沈碧玉撒娇:“我书包就在这儿呢,今晚住我哥家算了。”
沈碧玉本来不想让连年住这儿,奈何拗不过他,只好作罢。她转身要走,然后又注意到了画扇裙子上的那块污渍,不由得秀眉一皱,低低咕哝一句:“真是的……脏死了。”
这一句,连年和画扇都听清了。
睡到半夜,连年起来上厕所,他一直躺在床上想白天发生的事,迷迷糊糊的。
推开洗手间的门,连年伸手往墙上一摸,灯光亮起来的那一秒,墙角一个小小的蜷缩着的身影就突兀地映进了他的瞳孔里。
“谁?”连年吓了一跳,声音有点儿高,墙角那个影子抬起头来,连年认出来了,是画扇。
画扇缩在墙角,小脸上挂着洗衣粉的泡泡,两只小手浸泡在一个大大的盆子里,揉搓着什么。
连年的目光在她脸上滞了一滞,脸上挂着泡泡的她,倒还像个孩子,其实……蛮可爱的。
察觉到自己在想什么,连年不由得有些窘,他错开视线,因为怕扰到沈碧玉,就随手关了洗手间的门,往前走了半步:“你在做什么?”
画扇却像是忽然回神,几乎是被抓到了什么丑事似的想要把盆子往身后拉,连年俯下身,眼疾手快地摁住盆沿,看了一眼就发愣了:“你自己洗裙子?”
偌大的洗衣盆里,画扇在洗的,正是白天她穿在身上后来被弄脏了的那条雪白公主裙。
其实……她哪是在洗裙子,泡泡和水洒了一身,倒像是在洗自己。
看着画扇绷紧了的小脸和苍白的嘴角隐隐透露出的倔强,再看了看她小小的身子上狼狈的样子,连年莫名地有些生气,他没好气地指了指一旁的洗衣机:“你干吗要自己洗?”
说完这句,他才想起来画扇才九岁,以前必定也是家里的小公主,怎么可能会用洗衣机洗衣服?
下期预告:
“天易总裁遭车祸身亡,陆氏企业CEO念友情,愿意儿子娶程天易孤女。”
9岁的画扇竟然与陆齐安订婚了,到底什么情况?
治疗白癜风第一的医院白癜风可以医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