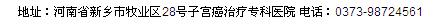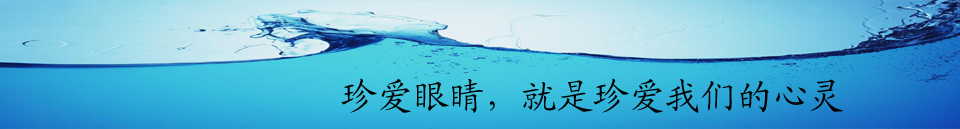
报大人生命的不完美,你必须顽强以对
作者|报大人|来源|好报原创
冬日的下午,翻看《皮囊》。掩卷之际,情绪竟长久沉浸在书页所勾勒的人生和情感里。
作者蔡崇达,一个以勤奋和才华在新闻业界搏得一席之地的30岁出头记者。但这本书并非他作为新闻人所看到的风光与奇妙世界。本书源自他的骨头,来自对生活的重新发现,尤其在父亲遭受八年病痛折磨辞世之后,他竟然发现,自己毫不了解父亲这样一位养育了他并曾经与他朝夕相处的人。
这本书里,他打开曾经关闭的内心之眼,来完成一项以前未完成的功课——打量他生命里出现的那些人。父亲,母亲,阿太,小镇上的发小,大学同学……看完与他有过交集的几个生命案例的工笔细描,你仿佛看到,命运大手操纵之下的生命图景,多么地无可奈何。
这本书的叙说有意无意指向了一个结论:生命并非一趟完美的旅程。我们可以对生活和世界怀有理想和想象。但现实中的世界,和你理想与想象的,其实根本就是两回事。
他笔下的父亲,前半生在生活中拼搏与努力,但人生的轨迹一路向下,在越来越小的生存空间中逐渐感到命运之手对咽喉的紧扼。最后,他病了,中风八年,得病之初,保持着乐观,与病魔相抗争,为生命尊严而战,但在强大的命运面前,终于宣告失败,退生为越来越胡闹、需要家人以很大耐心面对的“孩童”,直到最后离去。
他笔下的母亲,一个典型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安分女人,年轻的时候在中间人介绍之下,腼腆地看了一眼自己未来的夫君——也即“我父亲”,便选择了余生与他的命运相捆绑。哪怕他很穷,没有房子,也没有像样的嫁妆,只是约会时把她带到一片空地上,说:“将来我要买下这块土地,盖一栋大房子。”
后来父亲最大的成就便是在外地打工,带回些钱,买下了那块地,启动盖房计划。钱不太多,只能在那块地上盖起一栋较小较简陋的房子。并将自己与母亲的名字刻在石头上,竖在门口。这也是父亲此生最辉煌的时刻。因为“他实现了诺言”,而那之后,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生涯便进入下坡道,心情越来越不好,可以说这埋下了后来中风的心理引子。
而母亲呢,丈夫病了,两个孩子年幼,家中失去主动力,可谓悲惨,她得一边忙于生计,一边照顾一个病人,和一对未成年子女。却忽然有一天,她拿出辛苦攒下的一笔钱,不可思议地宣布——将父亲当初建的房子,进行扩建,建成四层楼!说它不可思议是因为,这套房子的宅基地已经被圈进小镇公路拓建规划,2年之内,这套房子就得拆。
母亲还是顶住各方压力,在大家的不理解之中,用辛苦攒起的血汗钱,“非理智”地启动了扩建工程。
后来,“我”终于理解,母亲可以受穷,但她忍受不了亲戚的冷眼和怜悯,她是为了一口气——她要证明,这个家庭是有能力生存得很好的!
再后来,“我”进一步明白,母亲这是在表达一份她永远也说不出口的爱情,她要建成小镇上最高楼房,让中风偏瘫的丈夫重拾光荣,恢复生活的信心,因为盖大房子曾是丈夫的梦想!
这是怎样的一种唐·吉诃德精神。
明明房子盖好后很快可能就面临拆迁,明明孩子读大学需要大笔金钱作支持……但她作了一项精神意义明显大于实现意义的决定,并行动起来。
当然这项举动,使得“我”,因此有了精神家园。每次在外打拼遇到障碍,心理压力巨大之际,“我”都一张机票,飞回家乡,在这栋楼房属于自己的房间里,舔舐伤口,恢复能量。
母亲的唐·吉诃德之举看起来并未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反而创造了“我”的精神家园,让卧病的父亲扬眉吐气。而此书中,还描写到了“我”的多个儿时伙伴,或大学同学,也用“理想”“想象”代替真实的生活,结果生命的列车滑进现实的深渊。“我”的近邻文展,小学时自命为天才,众人眼里勤奋上进的好孩子,做任何事情都带有计划性,并极力将自己培养成有领导力的人,在后来成长的路上却并未如自己的理想那样实现人生目标,甚至打不进大城市,作为失败者回到小镇上,做起了卑微的镇广播站播音员,并对“闯北京事业有成”的“我”因妒嫉而产生厌恶情绪。
另一位奇葩是大学时遇到的厚朴,他总是激情满怀地想要燃烧青春,在“我”看来却不过是什么时髦就热衷什么的一场戏梦之旅,他并没有真正找到自我,反而是通过一些过激的行动在掩饰骨子里的自卑。他组建校园乐队,也曾红火了一把,迎来了人生中的一次高潮,并成为众人追捧的校园明星,甚至还赢得了看起来能改变个人社会地位的爱情。
但最终证明,这不过是幻象。因为他的“成功”并不是建立在真正的自我认识及特长之上。因此很容易如风般消逝。果然不久以后,风消逝了,风光都成泡影,有地位的女神也抛弃了他。他却染上了一大堆恶劣的生活习惯,沉湎在自我幻象中越陷越深无力自拔。当“我”在北京正开始打开人生局面的时候,厚朴曾打电话,表示想来投奔,但电话在他过度敏感造成的不欢中结束。
后来,“我”接到了厚朴的死讯。他自杀了。他的精神出问题了,曾想去北京救治,但终未成行。
“我”反思到,其实,厚朴是死于越来越深的自我“想象”,他与现实严重脱节,无法真正认识自我,他的理想毫无现实根基,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曾想把北京当成自己的解药,寻求改变,但终未实现。
而“我”,不也是一个病人吗?
这么多年里,“我”由于父亲长期患病,为了缓解家庭困难,不得不自食其力,变成一个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奋斗者。在那些要么沉湎过度想象、要么失之于轻狂的少年伙伴中,“我”反而是一路顺利,成为“奋斗榜样”,获得了他们梦想而不得的人生——进入大城市,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但是有一天,一位师长的提醒,触发了“我”的内在醒悟——你要想想真正生活的答案是什么,好好地享受生活。
是啊,这么多年里,“我”是一位奋斗者,不断赢取生存所需的条件,“我”虽然不势利,但其实也在搏取成功搏取声名搏取成就感的过程中,忽略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作为记者,“我”就像一位坐在火车上的旅行者,窗外的风景快速掠过,别人的悲喜与我无关,“我”看起来是洒脱的人生观光客,实际上,是在选择一种逃避的方式。因为从窗户向外看到的风景、悲喜场面,虽然蕴含着不同的人生故事,而“我”却只是看客。
正是有了这种醒悟,才有了现在这本《皮囊》吧,这本书里,“我”不再是看客,里面记载的有关人性和生命的故事,因为用内心之眼在观察,悲悯地看到命运的无奈,确实具有震撼性力量。
此书中还有两个命运的故事也牵动人心,一个是小镇性感女人张美丽,这位大胆、独立的女性,因为过于大胆的恋爱故事受到小镇唾弃,后来远嫁他乡,再后来又离婚回到镇上,并带回来一笔资本,在镇上开酒楼、娱乐城,富贵显赫一时……但她始终还是无法被小镇上的人们理解,依然活在口水与鄙视当中,尽最大努力也无法洗去污名和“有罪”想象。最终,在宗族祠堂里撞墙自杀,香消玉殒。
另一个故事是香港阿小。由于父母在香港做生意,他在等待着被父母接到香港去居住。因为物质条件的优越、以及十足的香港范儿,他令镇上小伙伴自惭形秽,而阿小也以能移居香港为自豪的资本,表现得轻狂自傲。后来他果真移居香港。但若干年后,“我”去香港出差,却发现,香港远不是小时候想象中的天堂,在香港与阿小见面,也发现这些年他远没“我”想象的那么风光,他在香港大都市的人流洪潮中,只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求生存者。他父亲当年因生意破产,开车冲进了大海,家庭境遇因此一落千丈……
这本书里记录的一个个关于命运的故事,好像是在消解积极、乐观、奋斗、理想的意义。它仿佛在告诉你:虽然你可能对未来充满乐观,鼓起理想的风帆,但命运可能等着给你迎头痛击。你将来要面对的现实生活,绝非你现在所想象和规划的生活。医院的病房里,“我”也在努力搜寻这种残酷的例证,最逗逼、最乐观的病友老头,时时将死亡二字挂在嘴上当笑话讲,天天讲笑话逗得大家很开心,跟女护士开玩笑“晚上约会吧”,但有一天毫无征兆地,人就没了,去世了。而那个在圣诞节规违放烟花为了鼓励父亲闯过手术生死关的少年,他的父亲却在手术中去世……
这本书揭示出生命的苦涩,命运的无常。仿佛这才是生命常态。你的奋斗和理想,命运可能并不领情;而你在奋斗的时候,却忘了真正的生活应该是用来享受的。
这本书里唯一带来力量与冲击感的人物,是阿太——“我”的太姥姥,一位坚硬得像石头的女性,“我”多年里觉得她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她曾白发人送黑发人,送走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外婆。亲眼看着女儿的遗体被火化之时,别人都悲痛欲绝,她却斜视眼前场景,表情平静,若有所思。
迷惑不解的“我”后来问阿太,为什么在面对女儿遗体被火化时,她能表现得那么平静,阿太说了一句:“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
这句话“我”当时没听懂。后来90多岁的阿太,在临死前托人送话给远在北京的“我”:“黑狗达不准哭,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嘛,要诚心想我,我自然会去看你,因为从此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
这时“我”方才彻底领悟阿太的人生观: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阿太在艰难的人生中,锻炼了一副达观的生命态度。
这真是这本书里传递出的最大一丝光明——命运,你也许不可以改变,不可以违逆,但你可以选择自己对命运的态度,你可以在面对真实而残酷的人生时,拥有一种达观的态度。这会让你变得坚强。也让你可以享受到真正的生活。
一生坚硬如石头、90多岁去世的阿太,是这本书里的明灯,真正的精神导师。有了阿太的故事,这本书再苦涩厚重,也终算给了你一线希望——生命的不完美,你必须顽强以对。
报大人:好报主编。有时很温婉,有时是毒舌。飘零传媒江湖十数载,蹉跎成中年。仍在思考“长大后干什么”。有一天忽发奇想:做个北京最好的白癜风医院在哪里白癜风用什么药最管用